清晨六点,天光微熹,一座老城区的体育馆内已响起金属碰撞的清脆鸣响,七十岁的陈鹤松身着雪白击剑服,手持银亮长剑,步伐稳健地踏上剑道,他身形清瘦,眼角镌刻着岁月的沟壑,但眼神锐利如鹰,弓步、冲刺、格挡——每个动作都凝聚着四十年如一日的执着,汗水顺着护面罩滴落,他微微喘息,却笑着对记者说:“我的目标从未改变:站上世界击剑锦标赛的舞台。”
在中国体育以青年力量为主流的今天,陈鹤松的故事像一段沉默的传奇,退休前,他曾是机械工程师,用尺规绘制了半生精密图纸;退休后,他却以剑为笔,在剑道上勾勒生命的另一种可能,十年前,当同龄人开始含饴弄孙、钓鱼养花时,他重新拾起青年时代未竟的梦想——竞技击剑。“许多人问我,为什么要在古稀之年折腾自己?”陈鹤松抚摸着剑柄上的缠绳,目光灼灼,“但体育精神从不由年龄定义,剑道上的每一秒,都让我感到活着。”
他的日常如同精密运转的齿轮:清晨五点半起床,进行半小时核心训练后赶往体育馆,与年轻选手共同训练三小时;下午研究国际赛事录像,晚间则对着镜子反复修正动作,教练赵启明坦言,最初以为这位长者只是一时兴起,但陈鹤松用坚持打破了所有质疑。“他训练时从不要求特殊照顾,甚至主动增加强度,有次韧带拉伤,医生建议休息两周,他第三天就戴着护具回到了剑道。”赵教练展示手机里存着的视频:去年省级元老赛上,陈鹤松以一连串假动作晃过对手,剑尖精准击中有效区的瞬间,全场爆发出惊叹。
年龄带来的挑战客观存在,骨质疏松让他必须佩戴加厚护具,反应速度不及年轻人,体能恢复也更缓慢,但陈鹤松将这些转化为独特优势:“年轻选手依赖爆发力,而我更注重战术预判,就像下棋,你要读懂对手肌肉的细微颤动。”他专门研究老年运动员科学训练法,与运动医学专家合作定制食谱,甚至学习运动心理学以调整赛场心态,这种严谨态度感染了击剑馆的年轻学员——二十岁的省青年队队员刘雨辰说:“陈爷爷让我们明白,体育不仅是竞技,更是与自己的对话。”
陈鹤松的书房里,世界地图被彩色图钉标记得密密麻麻,巴黎、米兰、开罗……这些都是近年来他参加国际元老击剑赛的足迹,2019年,他在亚洲元老锦标赛中获得花剑组别季军;2022年,尽管全球赛事因疫情缩减,他仍通过线上模拟赛保持竞技状态,柜子里珍藏的十二枚奖牌旁,摆着泛黄的旧照片:1985年,三十五岁的他第一次夺得市级比赛冠军,那时他因工作繁忙被迫暂别剑道。“现在是把错过的时间追回来的时候了,”他指着世界击剑锦标赛的宣传海报,“那里有真正的高手。”

世界击剑锦标赛尚未设立常规老年组别,但近年来已陆续开展元老表演赛,陈鹤松与法国、意大利的老年剑客们组建了跨国交流群,分享训练心得的同时,也积极推动赛事体系的完善。“日本七十五岁的山田敏夫去年参加了世锦赛相关活动,这证明梦想并非遥不可及。”他打开电脑展示最新收到的邮件:国际击剑联合会正在考虑在2025年世锦赛中增设示范性老年组别。
这个梦想背后,是家人从不解到支持的转变,女儿陈琳最初担心父亲身体,如今却成了最坚定的后援:“看到他击剑时眼里的光,我们明白这是让他保持年轻的秘钥。”社区医院定期为他做运动机能评估,结果显示多项指标优于同龄人,医生笑称他是“颠覆老年定义的样本”。
夕阳西下,训练馆渐空,陈鹤松独自擦拭长剑,剑身映出他坚毅的面容,窗外,城市华灯初上,而他心中始终亮着一盏不灭的灯——那是伯尔尼世锦赛场馆的轮廓,是千万次重复练习指向的终点。“如果真能站上那个舞台,”他系紧鞋带,走向再次亮起的剑道,“我要让世界看见:只要心怀热爱,七十年不过是又一个起点。”

剑风再起,银光划破暮色,这条通往世界之巅的征途上,古稀剑客的脚步依然铿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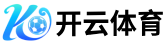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发布评论